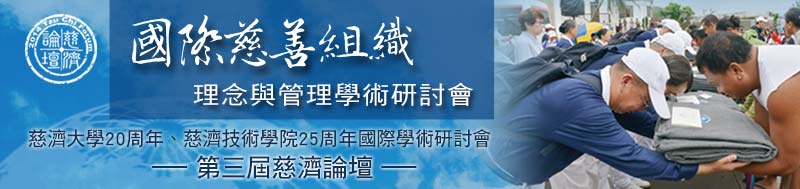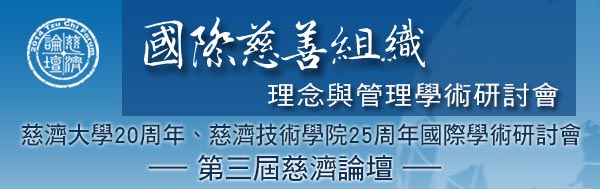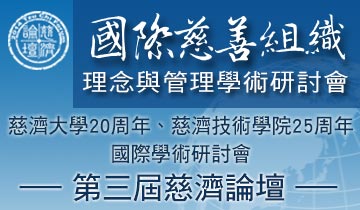莫拉克風災志工的持續動力
慈濟大學宗教與文化研究所 周柔含
1 言前
2009年8月7~9日,中度颱風莫拉克(Morakot)侵襲台灣,造成台灣南部與東部縣市嚴重水患。慈濟基金會立即動員全台志工,投入災區救災,經歷緊急、中期、長期三階段的急難救助與建村。
慈濟擁有全球賑災的豐富經驗,志工團體一直以「走在最前,做到最後」自許。創辦人證嚴法師也以賑災即「行菩薩道」,勉勵弟子;強調:「經者,道也;道者,路也。」也就是說,經典的價值意義,必須透過人的實踐才得彰顯與弘揚,而人的價值,也展現於實踐古德所訓之真理。
慈濟基金會發言人何日生曾指出:「慈濟學實踐的法門不是經由思想而思想,而是經由實踐而思想。」到底實踐背後的動力是什麼?「實踐而思想」的內容為何?佛教慈濟基金會,是一個佛教團體,從信仰出發進行社會服務;如果忽略其宗教性,漠視其背後信仰的動力,乃至無視於佛教教義的理念,則無法了解志工服務如何能產生善的循環。
面對莫拉克風災龐大的建設工程,志工如何解決內部人事的磨合,部分媒體的諸多負面報導,志工又是如何看待這樣的聲音?當志願服務已成為二十一世紀的主流價值,到底是什麼樣的力量,讓許多慈濟志工持續不斷,不計代價的甘願歡喜付出?
在災難現場,慈濟志工不談宗教,只談他們體會的信仰。本研究以參與莫拉克風災救助、援建的志工為對象,擬從內外考驗之間,探推動志工服務的持續動力。
§ 2 內外考驗之間
在災難管理中最困難的莫過於「垂直整合」與「水平協調」。災難發生後,諸多宗教團體、慈善團體同時湧入災區援助災民,然而各有自身的組織文化、制度與宗旨,再加上國家體制法令上的制限問題,地方政府與中央政府的溝通與職權,使的救災動員更加困難。面對台灣有史以來最嚴重的水患,政府或是民間慈善團體該如何合力協助,都是前所未有的考驗。
此外,面對巨大且緊迫的建設工程,全台志工從各地湧入,人力調度、物資運輸等都是未曾有的考驗。園區建設事項繁瑣,每日有一定的進度,橫向的協調,縱向的布達等考驗志工之間的和合。志工現場,有時候最困擾的是到底要聽誰的指揮;或當事情具急迫性,不好的聲色,經常是人事紛爭的起因,志工如何解決人的紛爭呢。
2.1 與災民的磨合
建設高雄杉林大愛園區永久屋的課題,在台灣是首例,且八十八天要完成七百五十六戶大型社區,一位耆老在入住時寫了一副對聯「慈濟人蓋大愛屋,太陽打從西邊起」,說明慈濟志工化不可能為可能。
永久屋的建設,參與以工代賑的鄉親具有多重身份,從受災的立場來看,他們是受災戶;從代工的立場來看,他們是受雇工人;從助人者立場來看,他們是受助者。面對如此大的災難,考驗著受災者與助人者。
志工對於原住民文化理解認知的有限性,再加上原住民對於異宗教的主觀認知,志工與鄉親的磨合是存在的事實。面對莫拉克風災援建過程,志工與原住民之間的磨合,志工如何因應;部分媒體的負面報導,志工如何看待這樣的聲音?
§ 2.1.1 軟實力:慈濟人文
災民排拒慈濟的聲音排山倒海而來,志工不受鄉親情緖言語的影響,幾位站在第一線與鄉親互動的志工皆表示,多年來的訪視經驗告訴他們,除了柔聲和悅、傾聽與陪伴之外,肢體語言往往比話語更有力量,握握他們的手,拍拍他們的肩膀,適時傳達證嚴法師最深的關懷,用愛化解,建立彼此的信任。
慈濟團體與原住民之間的摩擦,有些人認為是宗教信仰不同所致。事實上,宗教信仰的不同,不會是真正的問題,文化認知的差異,彼此相互了解不足,導致不甚信任,才是摩擦的起因。
中國文化的本源是以人為中心的,化解文化、宗教、人與人之間摩擦的最好處方,即是回歸到對人的尊重,人理的倫序,與人我之間的關懷。證嚴法師表示:「慈濟人文不是寫在書裡,而是寫在人的行動裡。」也就是說,慈濟人文即是在日常生活中,以最真誠「感恩、尊重、愛」的心,待人接物。
彼此不甚了解異族群的會遇,最好的方法即是以文化做為媒介,讓雙方彼此理解。為了讓以工代賑鄉親了解慈濟「工地人文」,安排有「人文營課程」。一位住民高度肯定「慈濟人文」,說:「在那麼多的慈善團隊裡面,都少了慈濟的一個靈魂,就是人文。」異文化的接觸,在不自覺中改變了人與人之間相處的方式,真誠的互信,才能促進彼此的交流。
志工以軟實力慈濟人文「感恩、尊重、愛」精神,陪伴鄉親,不談宗教,只傳達關懷,彼此相處並不涉及信仰,志工說感受到慈濟善意的鄉親告訴他們:「你們是上帝派來的。」這意味著,雙方從不了解到相互理解,從不信任到信任,不管是天使或是菩薩,彼此都是用真情意建立情感與信仰的交流,雙方都有所得。
§ 3.1.2 菩提願欲
諸多男性受訪者的話語中經常出現「使命必達」一語,每說到這四個字,聲調就高亢有力,讓人深刻地感受到他們堅定的決心。一位女性志工說:「如果你只想要當個快樂(按:輕鬆且不擔責任)的志工,你就不會有那種承擔的使命。」換言之,「使命必達」是志工共同的信念與默契。而默契與信念的背後是志工對證嚴法師的愛戴順服;對於所承擔的工作,志工都用實際行動完成他們的使命。
對於外界的批評,多數男性志工表示不去在意批評聲音,效法證嚴法師,回到最初助人的初衷,堅定信願,長養慈悲,菩薩道的人間正行,利他為上。相對於男性志工而言,女性志工則較傾向以柔軟的姿態,盡可能地直接向批評者澄清誤解。
菩薩道上的忍辱行難修,忍辱並不是一味地忍耐,真正的忍辱是需要無比的勇氣,含蘊著包容、容忍、寬恕、慈悲等美德。面對外界的批評聲,志工效法證嚴法師的精神,回到實踐本身──最初助人的願心,學習更謙卑、更堅韌,更勇敢面對現實。
《十住毘婆沙論》云:「一切諸法,願為其本,離願則不成,是故發願。」佛教的宗旨是出世的,佛教的方法卻是入世,大乘佛法更是以入世達成出世的目的。從菩提願欲中,湧出真誠、勇健的入世悲懷。由此而表現於事行,是人間的一切正行。
2.2 內部磨合
在志工路上,人與人之間因為情感的連帶而精進,也因為人與人之間的爭執傷和諧,「一定會踢到鐵板(按:遇到困難)」,幾乎是所有受訪者都有的共同經驗。所說的「鐵板」,指的是因人心、見解不同,不如其所願而産生的阻滯。面對人事磨合問題,志工如何藉境修心,藉事鍊心,解決人事問題。
2. 2.1 「靜思語」的指引
人與人之間情感的表達,最直接的就是面對面時的面顏聲調,柔言軟語容易拉近彼此的距離,建立相互的信任,不好的言語聲色則破壞彼此的情感。「慈濟十戒」,有一條即是要求「調和聲色」;這項戒律,在大團體中常受到挑戰。
「感恩、尊重、愛」,「知足、感恩、善解、包容」,「合心、和氣、互愛、協力」,「縮小自己」等慈濟語彙,已經成為志工組織互動的信念,提供志工思考問題,解決問題的依循,這些琅琅上口的話,堪稱是「慈濟行動規範」。保羅.田立克(Paul Tillich,1886-1965)曾指出:「在信徒團體中,宗教語言使信仰有了具體的內容」。面對人事的紛擾,多數志工們常會說「上人說」,事實上他們是回到「靜思語」,因為靜思語具有可實踐性,提供具體的指引,而不是抽象、形而上的概念。
透過「上人說」,將深奧的教理轉化成易解易持現代簡單明白的話語,産生了一種向上提昇的力量,弘大了生命價值與意義。因為當某個信念、想法、觀念在心中熱切活躍時,一切事物都會以此信念為中心,重新建構而新生。換言之,「靜思語」(上人說)是志工們的動力效能,行為的指標。
因為證嚴法師以身作則,讓「上人說」不是停留在理論,而是一種做得到的目標,是一種立身處世的指引,啟發志工自發向上努力的意願,在生活實踐中得到讓自己生命向上提昇的力量。
§ 3.2.2 組識信念:立體琉璃同心圓
證嚴法師表示:「信己無私,信人有愛;慈濟以戒為制度,以愛為管理,這就是慈濟的制度。」在慈濟志工場域裡,不論身分、背景、學歷高低,每一位志工各有位置,團體強調的是合作而非個人表現,尊重的是個人所在位置的職責,因此志工都可以在付出當中得到他的成就,這就是志工共事的「遊戲規則」。
所說的「遊戲規則」,即是「平等」與「尊重」,也就是「慈濟人文」,以人為中心的人理倫序。志工在利他中受到尊重與肯定,往往是持續服務熱忱的重要因素。證嚴法師提醒志工「碗有碗的功能,筷子有筷子的功能」,志工場域的運作猶如一部機器,每一個零件,乃至小小螺絲釘都有其功能,每一位志工都可以在所承擔的工作職責上發揮良能。
現今慈濟的人力編組,依其人數與區域範圍劃分成「合心、和氣、互愛、協力」,亦是證嚴期許志工應有的志工精神,「協力」組成「互愛」,「互愛」構成「和氣」,「和氣」匯聚成為「合心」。也就是說,「合心」之下有「和氣」,「和氣」之下有「互愛」,「互愛」之下有「協力」。每位志工的職責身分即是一個「點」(協力),不論是任何功能職責,皆回歸社區成為「線」,諸功能組的合作則成為「面」;僅管有人身兼「合心」幹事,事實上他仍歸屬於社區「協力」組隊的成員。
證嚴法師提出「立體琉璃同心圓」的概念,志工人人平等,意指從「點」到「面」,相互合作,形成立體的人間菩薩網絡,而所謂的「圓」,則是一種自我管理。因此,對外活動,志工不是代表個人而是團體;對內組隊合作之間,志工相互代表的是該工作角色之職責,而不是個人身分背景。這就是慈濟志工之間不用言說的共同默契。
儘管志工路上可能會有人事上的磨合,對志工而言,證嚴法師是這條道的帶領者,道的啟發者,在情感上志工內心對證嚴法師存有一份無比的恭敬心與感恩心,正是這一份恭敬心,讓他們不離這條道路。換言之,志工並不是依「動員」來聚集人力,而是自發性投入的集體行為;再如上,「戒」與「愛」的自我管理制度之紀律,才是組織運作順利推行的重要驅進力。
其次,社區裡有極細緻的任務分配與承擔責任區,志工網絡分部在社區各個角落,平日已落實「小組關懷,多組活動」制度,數數集會,聚做眾事,調和默契,增長信念。此外,志工平日透過各種管道如大愛電視台、慈濟網頁訊息等,知道慈濟事,有助於團體凝聚力的提升,無形之中已經養成很好的共事默契。
即使有人事考驗,仍有志工成員讚歎「慈濟的美,美在參差不齊」,儘管志工來自四面八方,人人在此有成就;志工說「慈濟的美,美在人人一念善」,這正是志工動力的根本。
下節擬從「持續的動力」探討,到底是什麼樣的力量,讓志工不畏困難,精進不懈,意志堅定行在志工服務的道上。
§ 3 持續的動力
本文受訪的志工大部分都是已經受證的慈濟委員或慈誠,一半以上的受訪者曾經參與過九二一、華航空難等救災活動。他們參與杉林大愛園區建設,是慈濟因緣種子早已成熟且落地生根。
多數的志工都是被證嚴法師的悲心所啟發,被她的言行模範所召喚。所經驗的這一切,都是個人情感經驗的真實感受。對志工而言,那樣的經驗與情感,真實且深刻,促成了他們成為志工的重要助緣。
然而,菩薩道上難行能行,究竟志工們是如何堅持在這條道上呢?人間佛教講的修行並不是一個有形的圃團座具,而是生活實踐,是沒有條件的,但是並非沒有目的,因為修行本身即是目的。因此,離開實踐向度,或現實性的討論,純粹只是知識;反之,直接從行動者現實生活的實踐經驗去探索,才能碰觸到行動者本身內在最深層的情感,與真實連結。
§ 3.1 實踐生信
聖方濟(Francis of Assisi)言道:「一個人只有將其知識化為行動時,才算真正擁有知識。」 證嚴法師表示:「要讓菩薩精神永遠存在這個世界,不能只有理論。」簡而言之,唯有透過實踐,才能讓菩薩精神留存在人間。
灰衣志工阿宏提到自己和以工代賑鄉親之間的相處,從原本討厭,更質疑「普天三無」是件不可能做到的事,最後不僅是態度轉變,更從踐行中斷疑生信,體驗到真實的喜悦與慈悲。事實上,阿宏的「法喜」是源自於在「做」中放下自我的體驗,對他而言不只是挑戰自我的成功,更賦予自身內在力量,從中信受。因此,「實踐生信」的法喜經驗,是驅動志工持續助人行為的重要動力。
「做」,是一種確定方向的態度;「賺歡喜」,是許許多多志工的真實寫真;那是一種「無所求」的「法喜」,「如人飲水,冷暖自知」。歡喜的是內在價值──愛與慈善,那種「樂在其中」單純的喜悅,就是實踐存在的方式。
「佛法大海,信為能入,智為能度。」「信」,既難且容易,常云「信解行證」,縱然最初不相「信」,倘若經由自身實踐體認到的,與經典教理、教說相應,一定會回到「信」。
信是慧的前階段,實踐生信的「信」,將成為下次行動的力量;一旦成就慧的同時,「信」的意義也就消失,然而這並不是意味著菩薩道的修行不需要「信」,而是原初的「信」(skt:śraddhā;confidence)已經轉為心澄淨的「淨信」(skt:prasāda;pellucidness),達到「信智一如」。
§ 3.2 敬信而行
現代神學之父、宗教哲學家施萊爾馬赫(Friedrich Schleiermacher,1768-1834)曾指出:「宗教的本質既不是思維與行動,而是直觀和情感。」
對志工的「直觀」而言,筆者認為那是發自於內在某種情操而付出行動的直接經驗,它和某種內在情感相聯繫,但不是模糊朦朧抽象的感覺,而是具體有明確的內涵,對個人是實存的、真實的,且會有意無意地影響了個人的內在意識──更深沉的情感,即信念,這樣的信念會牽動一個人整體的存在,成為信仰。也就是說,如果在宗教經驗裡沒有生起情感,則不容易喚起信仰;換言之,沒有情感性的宗教經驗,便談不上信仰。
情感會帶動信仰的產生和深化,在這個慈濟大家庭中,證嚴法師是牽動慈濟情的源頭;表面上看來,志工似乎是因為證嚴法師,或者是說對於證嚴法師的情感使然。事實上,志工對於證嚴法師的情感,不在神祕的宗教經驗,在於證嚴法師自律嚴謹的人格典範,那是志工自身經驗的直觀而産生的情感,進而産生內在「宗教大家庭」的依附關係──一種深刻持久情感的連結。
「信為道元功德母,增長一切諸善法。」很多志工表示會持續在這條道上,是因為認同證嚴慈悲大愛的理念與受到證嚴法師無私的精神感召。諸多志工們對證嚴法師的愛載敬服之情,顯而不藏;愛載是基於「信」,「敬」服是因為「慚」已不足。自身多年來的志工經驗,讓他們更加堅信,這是一條正確的道路,他們的信不是世俗上認同的信,而是透過自身實踐從內心生起一種虔敬情感,願意全力信隨,無怨無悔。這份單純的相信與共識,敬信而入,是多數志工持續的動力,讓他們不畏人事挫折,自發性地共同行在菩薩大直道上。
保羅.田立克指出:「信仰絕不是由意志創造出來的。接受與臣服信仰的決心,是使信仰臻至忘形境界的要素,但不是信仰的成因。」 表面上讓志工産生「內在的接受與臣服」的是因為對證嚴法師的「敬信」,而促成他們投入志工行為的動機。事實上或者應該是說,因為志工的行動意向,才構成他們真正的信仰;因為具有明確的行動意向,有具體的志工行為,而不是單純的信而已。重要的是,那不止是一種意志的服從──「敬」,外在的志工行為更深深地影響志工的內在,一種心靈的歸順──「信」。如果沒有這些具體行動意向,則無法構成信仰。
佛法從恭敬中求,「敬信」是修行的重要動力,更是受持佛法的基本要求與善根。綜合來說,理性是信仰的前提,信仰是理性的實現。信仰包括情感因素,但是僅憑情感無法構成「信」。志工的「敬信」,不止來自某種強烈的情感,更在情感之上透過生命,理智地洞悉人生的價值,敬信而行。
§ 3.3 同事度
《宗教的慰藉》作者艾倫.狄波頓指出:「現代社會最深切感受到的一項匱乏,就是社群意識的欠缺。」 Mc Millan和Chavis認為:「所謂的『社群意識』,是指在團體中産生與他人連結及歸屬感,彼此影響他人,或受他人影響,於互動中分享彼此故事與經驗,滿足彼此需求,藉由彼此的承諾而產生的信賴感。」在現代化的社會中,傳統組織與價值瓦解,家庭與工作都無法滿足人對人際網絡建立的基本需求。宗教即是社會的縮影,宗教團體除了完成宗教功能之外,更彌補了現代社會所欠缺的「社群意識」。
慈濟志工對外活動常以手語帶出「我們都是一家人」,拉近彼此距離,這種沒有血緣關係擬親屬的家人法親,即是佛教「四攝法」(布施、愛語、利行、同事)所說的「同事攝」。
是什麼力量讓志工願意持續在志工道上?許多志工表示「應該是同事度」。所謂「同事」,即大家以平等的身分,做同樣的事,同甘共苦;倘若有人做惡,能令自己融入對方所處環境,進而引導讓他同於自己行善,即本節所說的「同事度」。
雖然許多志工提及人事磨合問題,但是並非不可避,或人人會碰到。筆者常常感受到許多女性志工彼此之間的情誼更甚自家姐妹,男性志工之間情同手足,相互謙讓。女性志工強調,志工路上一定要有相知相惜的同修道友,彼此相互提攜。這份同行的默契與情意,對彼此同在團體裡的認同,建構了現代社會所欠缺的「社群意識」。
為什麼精進在志工道上?許多志工說「因為我們家師兄」、「因為我家師姐」。也就是說,能夠持續在志工的道上,是因為家人的影響。修行道上,雖然互為夫妻,但是已是「同事」關係。除了家人,還有法親的力量。不像工作職場的同事,或屬長官部下的上下關係,志工場域的「同事」沒有利益上的牽連,或有主從關係,工作上相互配合支援與承擔,互相牽引帶動。團體是個人的組合,個人與團體相互影響,團體的力量大於個人,久而久之,個人的行為、價值觀會以團體為依歸,自然生成一種情感的認同與歸屬。
團體的融和健全,以和合為基礎,釋尊依律制攝僧,其綱領即「六和敬」;這樣的和敬思想,適用在任何團體。志工共事時,尊重他人及其想法(見和同解),遵守紀律、和睦相處(戒和同行),「有福同享,有難同當」(利和同均),自然也就有身和、語和、意和的和合表現。志工從零開始建立的默契和法親情誼,有時更甚血緣的兄弟姐妹,為利他而努力,相互敬重,和合攝受,共同學習,增長善根。信念與實踐,讓他們彼此安住、精進在菩薩道,即「同事度」。
§ 3.4 能詮的教法
佛法的流傳與化世,賴於佛教徒的身教和言教,即本節所說的「能詮的教法」。不同於對證嚴法師的敬愛之信,或是從會員轉換成為慈濟志工的受訪者,原初對慈濟團體完全不了解,卻立即成為慈濟志工,而且願意再持續的原因仍是在於自身接觸慈濟團體的經驗,不論是團體的氛圍,或是人與人之間互動,都讓他們留下不同過往對宗教團體既有的印象,秩序與和諧所展現的人文之美,是促使他們走入慈濟團體,成為助人者的重要因素之一。
證嚴法師表示:「能感動他人的人,即『人品典範』,所做的事都能『文史流芳』」,就是慈濟的人文。」工作技術面的學習容易,但是精神風範的傳承卻必須透過人與人之間的互動去感受而習得,進而產生理念的共識與情感的連結,這是推動志工繼續往前,齊心協力的重要因素之一。
前輩志工樸實無華的身教,溫和蘊藉的態度,簡單的言語,在自我規範中,將佛法落實於生活,是後輩學習的典範,即慈濟人文理念「人品典範」的具體實踐,顯現的是「能詮的教法」。人間佛教的開展,佛弟子的人格風範,能夠發揮言教與身教的感召力量,影響更多人持續在菩薩道上。
§ 3.5 生命轉化
志工行為,有的是因為本身內在生命態度而驅動善行,有的是透過志工行為昇華轉化內在生命價值。生命轉化,由內化而外顯,由外而深化內在,內在生命經過不斷歷煉方能臻於成熟,活出新的生命價值。
多數志工帶著個人背景、問題走進志工行列,透過志工服務與不斷地學習與成長,漸漸改變自己,從與人互動中産生自信,再加上如自家人般的法親情誼,滿足自我成長與自我實現,找到自我存在的快樂。筆者認為,志工的生命轉化,根源在於慈濟人文以「感恩、尊重、愛」為重點的教化。
吳怡指出:生命的轉化系統有兩方面,一是平行的轉化,一是上達的轉化。前者說的是個人內在的轉化,突破自我,受容他者;後者是承續前者,進而由下向上提昇自我,並影響他者,此二者的轉化過程,是不斷地相互融合。
具體來說,志工藉由境教的學習,一種從被動的感受,改變了自我的習氣等,這是平行的轉化;進而成為自發行為,是一種主動的精神提昇,展現出不同於過往的自己,與他人締結和諧新關係,活出全新自我,意味著自我成長、自我實踐,「生命轉化」後的新生,讓生命更有力。
簡而言之,志工場域人事的磨練所帶來的是更有能力接受自己與他人,從個體的修養,相互關係,互相影響,這是一種人與人之間平行的轉化,進而產生一種集體向上的力量──社會的教化作用,讓志工豐富了自己與他人的生命,這是一種上提的轉化,同時不失個人信仰。
真正能夠在佛法中得到利益,不管是深是淺,多是從內心發出感恩心而獲得,如果缺少了感恩之心,不易從佛法中獲得法益。多數志工因為感恩,感恩他人成就自己,而願意再付出,讓生命有了不同於過去的寬度與亮度。
§ 4 結論
慈濟基金會是一個宗教團體,對於「宗教」,證嚴表示「宗就是人生的宗旨,教就是生活的教育」,必須將「佛法生活化,菩薩人間化」,簡單的話語道出了落實宗教真實理想的方法。
從內文的討論,可以明白志工服務是在現實生活中實踐聖人之教,實踐一種普世價值;並在普世價值的實踐中,內化德性而向上提昇,生命轉化而蘊育出一種生命態度,進到生命的核心,並從生命的核心産生一種新的力量,持續實踐「道」的普世價值。
佛教的宗旨是出世的,佛教的方法卻是入世。面對異宗教、異文化匯流之際所産生的種種磨合,志工學習以愛化解,並以實踐軟實力「慈濟人文」精神──感恩、尊重、愛,做為解決問題的方式。面對外部負面聲音,志工效法證嚴回到最初助人的初衷──菩提願欲;「願為欲依,欲為勤依」,視種種考驗為修行。
面對內部人事的紛擾,志工習慣性地將自我交付給「上人說」,事實上他們是以「靜思語」為依歸。這些慈濟語彙,已經成為志工組織互動的信念,提供志工思考、解決問題的依循,堪稱是「慈濟行動規範」。因為「靜思語」(上人說),具有可實踐性,讓「道」成為一種的行為規範。
「立體琉璃同心圓」,是證嚴法師提出的組識信念,在組織裡人人平等,相互尊重,因此志工都可以在付出當中得到他的成就,這就是志工共事的「遊戲規則」;對所承擔職責負責,相互支援,恪守「戒」與「愛」的自我管理制度之紀律,實踐不用言說的人文精神,這是慈濟組織運作順利推行的重要驅進力。
皮耶•布迪厄(Pierre Bourdieu)表示:「實際的信仰不是一種心智狀態,更不是一種對一套的教條教理的武斷服從,而是一種身體狀態。」那樣的「身體狀態」,是思想與實踐的合一,帶著精神情感,是一種「生命轉化」的身心狀態,將成為下次行動的根據。
無論策動精進的動力是什麼,或因「實踐生信」,或因「敬信而行」,或因「同事度」,或因「能詮的教法」,乃至「生命轉化」。綜合來說,信仰的實踐,包含了宗教實踐與社會實踐。宗教實踐,就志工個人面向來說,即是道德實踐;就社會運用的面向來說,是一種善的形式的堅持,即社會實踐。
當「大愛」成為信仰,志工願意投入終極關懷,轉以一種善的「生活實踐」形式──「志工服務」存在,日日不息。換言之,志工藉由志工服務──人間正行,修菩薩大直道,轉化生命,實踐信仰,是助人者也是最大受益者。
引用書目
經典
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(CBETA, T09, no. 278)。
《大智度論》卷1 (CBETA, T25, no. 1509)。
《十住毘婆沙論》(CBETA, T26, no. 1521)
期刊論文
Saddhatissa, H.(1978),The Saddha Concept in Buddhism, The Eastern Buddhist Vol.Ⅺ No.2, pp. 137-142.
Mc Millan, D.W., & Chavis, D.M. (1986). Sense of community: A definition and theory.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, 14(1), 6-23.
楊永年(2009),〈八八水災救體系之研究〉,《公共行政學報》33,頁150-151。
黃智慧(2012),〈「多元文化」理念的脆弱性:莫拉克災後重建政策思維、法令與組織型態〉,潘英海主編《再現南臺平埔族群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》(國立臺灣博物館),頁50-52。
專書論文
周柔含(2014)〈佛教志工「行經」經驗探討――以莫拉克風災慈濟志工為例〉,《山窮水盡見真情--莫拉克風災慈濟援助的實證研究》。
專書
Paul Sabatier (Ed.)(1898), Speculum Perfectionis, Paris.
Paul Tillich(1959), Theology of Culture, Oxford University Press.
吳怡(1996),《生命轉化》,(東大出版社)
保羅.田立克著,魯燕萍譯(2000),《信仰的力量》(桂冠出版社)。
威廉.詹姆斯著,蔡怡佳、劉宏信譯(2001),《宗教經驗之種種》(立緖文化事業有限公司)
何日生(2008),《慈濟實踐美學》(上,立緒出版社)。
施萊爾馬赫著,鄧安慶譯(2009),《論宗教.對蔑視宗教的有教養者講話》(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道風書社出版)。
艾倫.狄波頓著,陳信宏譯(2012),《宗教的慰藉》(先覺出版社)。
其他
《慈濟月刊》(332期,1994)。
高信疆編(1989),《證嚴法師靜思語》(九歌出版社)9。
網路資源
慈濟基金會網頁http://tw.tzuchi.org/projects/88flood/index.php?option=com_wrapper&view=wrapper&Itemid=198(2013/02/05)。